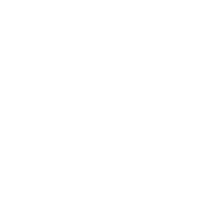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
|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简介 | |
|
|
|
|
说起狂怪,在泰州历史上有两个人值得记取:一个是郑板桥,一个是王艮。郑板桥的诗、书、画艺术“怪”字当头,逸闻趣事也流传下来不少,人们早就耳熟能详,自不必在此多说。王艮,一位出身低贱、生活寒苦的盐丁,靠自学起步,“狂”字当头,在中国哲学和思想史上开门立派,闯出了一片天地,尽管比郑板桥早出生整整二百一十年,却未必普遍为人知晓。
真要探究起原因来,也并不使人难以理解。郑板桥从事的是人见人爱、风雅高致的艺术行当,就是不怎么在行的人,也想拿过来卖弄一番。王艮可就不同了,他研究的是“哲学”,一个想起来就让人望而却步的字眼,高智力的学问,仅仅受过四年童蒙教育、小学还不曾毕业的王艮却敢向它发起攻击,并最终成名成家,导引出了一个学派的兴起。你说他狂不狂?他的“狂”,有点出人意料之外,他的成功,更让人意想不到,他的思想,别有一番滋味。与板桥比,王艮“狂怪”得毫不逊色。单就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将思绪返回到五百多年前的明代,去认真地追溯一番了。
一、人生素描 明成化十九年(1483)六月的一天,天气已经相当炎热,正是煮盐晒盐的最佳季节,在泰州安丰场的一个贫苦的盐丁家中,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就是后来成为一代哲学大家的王艮,父亲给他取名银,希望他能够发家致富,给贫寒的家里带来财运。 有必要在这里对盐丁作个交代。盐丁是对从事盐业生产的劳动者的统称,因为从海水中炼盐,往往要设亭立灶进行煎熬,盐丁又被称为灶丁、亭子或亭丁。盐丁的家庭叫作灶户或亭户,从唐代以来就有了,由政府划定,在盐场设灶煮盐,有时也把一部分囚徒补充进来。这是一个地位低下、倍受歧视的阶层。盐丁从十五岁起至六十岁止,每年要向政府交纳一定数额的盐课。盐丁的生产条件极为恶劣,他们不但“拮手裸体,劳筋苦骨”,而且由于长年的烟熏火灼,许多人的眼睛都失明了。王艮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慢慢长大的。 王艮七岁入私塾读书,学的是儒家典籍《大学章句》,因为家境贫寒,十一岁就辍学成了一个盐丁。四年的启蒙教育,对于一个童稚未脱的孩子来说,很难说能学到多少东西,就是记下了儒家经典中的只言片语,恐怕也难以消化得了。这些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在于似懂非懂的《大学章句》,不知不觉中在王艮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崇尚儒学的种子。转眼八年过去了,盐丁生活的艰辛、人身的低贱在王艮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特别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也许是父亲不忍心儿子重复自己的生活,十九岁那年,王艮奉父命外出经商。一旦有了适宜的土壤,心中埋藏已久的种子马上破土而发。王艮“以山东阙里所在,径趋山东”,“阙里”是春秋时孔子住地,在山东曲阜城内阙里街。经商之暇,王艮特地到孔庙拜谒。我们很难想象王艮初到孔庙时的那种激动和崇敬,不过,那声“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的慨然豪叹,越过五百多年的茫茫时空,似乎仍然在耳边回响。王艮选择到山东经商,显然是为了续接八年前的那段儒学情缘,情感的成分是非常明显的。 有人说王艮的经商活动,其实就是贩卖私盐。究竟是否如此,已经不再重要,也无从确证了。王艮的经商活动,大致持续了十年左右,由于他经营得法,家境也日益富裕起来。这为他日后的学术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 王艮是一个有才智、有抱负的人。他的理想并不是终身为陶朱公,而是要当新孔圣。“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的那声豪叹,其实已经为他的一生定下了基调。正德二年(1507),二十五岁的王艮再次拜谒了孔庙,“奋然有任道之志”。在明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后期,对孔子的尊崇是十分隆重的,面对孔庙那古柏参天的肃穆氛围与拜谒者的虔诚态度,都会令人对孔子千古不朽的盛名产生仰羡之情,就像当年刘邦与项羽见了秦始皇的赫赫威势那样,顿生“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效法之志。只不过作为一般人来说,这种想法只是昙花一现,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消弭于无形。而王艮却没有,他认真起来了,回去后即“日咏《孝经》、《论语》、《大学》。置其书袖中,逢人质义”,“默坐体道,有所未悟,则闭关静思,夜以继日,寒暑无间,务期于有得,自是有必为圣人之志”。他完全靠着先天的颖慧,孜孜地四处求教,静静地体悟思考,从而慢慢地达到了哲人的境界。 王艮二十九岁时,做了一个非凡的梦,梦境中天坠落下来了,地上无数的人奔号求救,只见他王艮先生奋然上前,高举双臂,一手托着天穹,一手把乱了次序的日月星辰重新排列归位,众人在他面前欢歌起舞,纷纷拜谢,大梦醒来,王艮不免又惊又喜,大汗如雨,顿觉心体洞彻,万物一体,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神圣感油然而生。他感到这个梦对他太重要了,于是极其慎重地记下了做梦的时间:“正德六年间,体仁三月半。”从这以后,我们已经看不到盐丁王艮,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头戴五常冠,身穿深衣大带,手执笏板,“言尧之言,行尧之行”的当代奇人。真不知道穿着这身奇奇怪怪的行头走在泰州大街之上,会招来多少异样的目光,引起多少人窃窃私语,他们真的会相信这是一位得道高人吗? 也许说他“得道”确实还早,凭他现有的水平,让他去钻研《四书》、《五经》,领会其中的微言大义,确实也难为他了。但王艮自有办法。没有老师,他就“逢人质义”,以路人为师;章句难解,他就闭门体悟,“信口谈解”。恰如一张白纸,可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王艮知识素养的限制,正好使他免于自古以来陈词滥调的影响,他的每一点见解,都是打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清新而嘹亮,恰似一曲天籁之音。更可贵的是,王艮总是把“精思”与“躬行”结合起来。学了《孝经》,就力践孝道,替父亲外出服劳役;学了家礼,就撤去家中佛像,改祀四代祖先;学了《礼经》,就马上制作并戴上代表仁、义、礼、智、信的“五常冠”,穿上仅袖口周长就有二尺四寸的又宽又大的“深衣”;立下了“以先觉为己任”的志向,就立即在家乡教授平民百姓,启迪“后知”。 这些平常人看来狂怪荒诞的行为,多少有点虚张声势,但王艮是认真的,你看他执著地向前走着,毫无作秀之嫌。 当王艮偏处泰州一隅,游走于大街小巷,乡野田间,一心一意地经营自己的圣人梦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有一位出生于浙江余姚的阳明先生,其学说已经风行江南,直到有一天有人听了他讲的《论语》首章以后,说他与阳明先生的观点十分相似,惊讶之余,他才决定去会一会这位与自己同姓的阳明先生。谁知这一会,竟然给他会来了一位“名师”,为他开启了一个新的学术境界。
王艮是自信而自负的。他到南昌拜见王阳明并不是冲着拜师去的,他要看看自己的见解与阳明先生究竟有什么异同,他要看看这位领引江南的阳明先生究竟有多大能耐。所以,两人一见面,就“相与究竟疑义”,直至“纵言天下事”,反复论难起来。几个回合下来,王艮的座位也随着由上座而侧座而下拜变了几次。但王艮可不是那种轻易服输的人,当听了王阳明讲了“致良知”的心学宗旨后,当下佩服得了不得,“乃下拜而师事之”,可回到宿舍以后,又感到自己考虑不周,拜师太轻率了,第二天又过去与阳明论辩一番,最后才心悦诚服。 王艮服膺王阳明,但并不盲从,该坚持的他还是坚持。当论及“天下事”时,两人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王阳明:“君子思不出其位。” 王艮:“某草莽匹夫,而尧舜君民之心未尝一日忘。” 王阳明:“舜居深山与鹿豕木石游居终身,忻然乐而忘天下。” 王艮:“当时有尧在上。”
王阳明要王艮安守本分;王艮却说自己虽然是平民百姓,却始终在追求尧舜时代的理想政治;王阳明说,你不是追求尧舜时代的理想政治吗,那就应该像舜那样勤奋劳作,欣然自乐而王天下;王艮说,现在不是没有像尧那样圣明的君主吗。大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概。 其实,正是王艮的这种独立思考、不轻盲从的态度,使阳明先生大为赞赏,难怪事后王阳明对门下说道:“向者吾擒辰濠,一无所动,今却为斯人动矣。”于是,他给这个从泰州远道而来的学生,改名为艮,又取《易·艮卦》“艮,止也”之义,命其字为汝止,教育王艮行止得当,动静适时。在阳明先生的悉心指点下,王艮接受了心学的基本思想,并最终成为王阳明的得意门生之一。 王艮从阳明先生那里领会了心学的基本思想后,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该信奉这一绝学,而老师的学说似乎只局限在南方,他感叹说:“千载绝学,天启吾师,可使天下有不及闻者乎?”便慨然有到北方代师传道的意思。王艮是那种知行合一、说干就干的人,主意一定,他就坐着自制的仿古轮子车,一路讲学直到北京城,颇有孔子周游列国的古风。尽管这次北上讲学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他这种古风式的讲学,和敢于招摇天下的行为,还是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所谓“人人以怪魁目之”,回头率当然也特别地高了。尽管王艮意气太高,行事太奇,用世之心太热,并因此受到阳明先生的斥责,但他日后能够开阔阳明之学的源流,并且自成一派,却是与此大有关联的。 王艮师从阳明先生近十年,终究没有改变他一心求圣的狂者人格,但他不仅从阳明那里印证了自己的心悟所得,而且阳明的心学理论更加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可以说,正是王艮自身的狂者气质与阳明先生影响的结合,才促成了一代大师的诞生,并由此催生了泰州学派。 王阳明去世后,王艮开门授徒,开始了他“自立门户”的讲学时期,亦即泰州学派的奠基时代。在这个时期,王艮定居于自己的家乡安丰场,主要从事讲学活动。前期外出较为频繁,多游于江淮间。晚年居家讲学,从学、造访者不绝。
泰州崇儒祠 也许是求道太过用心、传道太过辛苦,王艮病倒在讲席上,于嘉靖十九年(1540)冬天去世,终年五十八岁。放眼望去,他所开启的泰州学派,由颜山农、罗近溪、何心隐、李卓吾继承,前仆后继,个个都是棱角分明、卓绝百代、响当当的风骨人物。 王艮先生,可以瞑目矣。 二、思想影像 首先的一个问题是,作为一介平民的王艮的思想何以能在思想控制比较严酷的明代产生,并表现出特有的生机和活力? 不妨慢慢道来。 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一直重视对人们精神的统治。秦始皇焚书坑儒,他嗜好的是法家。到了汉代,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由此取得了绵延二千多年的统治地位,特别是发展到宋、明时代,作为儒家学说代表的程朱理学更成为一种思想的钳锢,“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成了摧残人性、限制人自由发展的代名词,其消极和弊端日益显现出来。情况在晚明似乎发生了转折,时代显然已经不再由铁箍之下的理学主宰,日常生活的观念,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当世宗们一心沉醉在设蘸祷告之中,祈求上天赐予长生不老的时候,朝廷大臣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幡旗飘荡的西苑里,反复书写空洞无聊的青词,讨得皇帝的欢心,以儒学经典为根据的理学,作为一种政治和生活的信念与准则,从封建社会的上层开始,便已徒有其表,不能切实遵守奉行,整个社会已失去了儒学道德的精神规范,逐渐走向病态和没落。正是这样一个从根子上已动摇和失范的时代,才给王艮提供了相对宽松和自由的发展空间,使他能够轻松地游走于乡野民间、城市街巷,孜孜不倦地向人们宣讲他“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进而形成一股颇具声势的思想潮流。 在思想禁锢、个性萎缩的时代,王艮的思想具有思想革新和个性解放的积极意义。 儒家伦理思想以人“性本善”为基础,以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的“四心”确定了仁、义、礼、智“四德”的心理基础,认为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是人生最有价值的、第一义的。与之相关,人生命中的其它东西都是第二义的,甚至是丑恶的。所以,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就在于人有仁、义、礼、智,人只有通过发展它们才能真正成为人:“人之所以异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当仁、义、礼、智被后人演绎成三纲五常并运用到现实生活中的时候,就成了压抑人的欲望的非理性的暴力工具,并最终发展到“饿死是小,失节是大”的吃人理学。 王艮说:“天性之体,本是活泼;鸢飞鱼跃,便是此体。” 鸢飞鱼跃,春分桃李,河川奔流,皆是自然。同样,人的生命欲望、生命冲动也是自然所赋予,人应该过一种合乎自然的生活,按照自己的本性去生活,就像自然界的春华秋实一样。王艮显然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然而然的,并无善恶之先天规定性,与之相应,人的七情六欲都有存在的合理性。由此引起了他对“天理”、“人欲”问题的重新思考,他说: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
“天理”、“人欲”是宋明理学中最基本的观念。“天理”一般是指忠、孝、信、仁等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总称;“人欲”一般是人的物质欲望和生理生活的需求,即所谓“饮食男女”之事。在宋明理学那里,“人欲”必须服从于“天理”,如果两者发生冲突,就应无条件地“存理灭欲”。 王艮以“天理”为“天然自有之理”,实际上等于“认欲为理”,把人的物质欲望和生理需求看成是“天理”的一部分。宋明理学所谓的“天理”和“人欲”在王艮这里泯灭了界线,得到了统一,而干扰、破坏这种“天然自有之理”实现的因素则成了王艮心中真正的“人欲”。 王艮把“天然自有之理”称作“天理良知”。当王艮把自己的学说一以贯之到实践中的时候,便形成了在中国思想史上颇具独创性的“百姓日用之道”。 王艮“百姓日用之道”的基本特点,就是不分贵贱贤愚,而以“百姓”为本位,把是否合乎“百姓日用”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甚至作为检验是否“圣人之道”的尺度。在他看来,凡是合乎平民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的思想学说,就是真正的“圣人之道”,否则,就是“异端”。 儒家传统思想总是把“圣人”和“百姓”区别开来、对立起来,进而把“圣人”及圣人之“道”加以神化。王艮不然,他的“百姓日用之道”则是力图填平圣、愚之间的鸿沟,把百姓日常生活提升到了“道”的精神层次,而把传统神圣化的“道”拉下神坛,与普通百姓的生活融为一体。值得注意的是,王艮提出的“即事是学、即事是道”时,强调了“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这种要求摆脱贫困,争取人身生存权利的观点,是王艮“百姓日用之道”及其社会理想的基本出发点。 “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代表的无疑是平民社会的精神利益,它以其强烈的启蒙色彩,对十六世纪的晚明社会形成了强大的冲击,为日益增长的平民社会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基础和道德庇护。 我们姑且不去探讨它对传统尊卑价值观是怎样的颠覆,仅仅是活跃在晚明思想界的那些陶匠、木匠等布衣学者就足以表明它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社会风气。 王艮不仅关心人的物质生活,而且关心人的人生价值。人的价值一般表现在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两个方面。传统儒家从维护政治权威和封建家天下的凝聚力出发,长期宣扬社会价值高于个人价值,个人往往处于被“遗忘”的角落。自南宋至明末的四百年间,理学统治着思想界,不惟个人意志不可能自由表达,就是人适当的生命需求也被剥夺。对个人生存空间的极度挤压,必然带来人生价值天平的失衡。王艮发挥独信自家良知的自由精神,打破天理桎梏,以自我作为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 他宣称,“我命虽在天,造命却由我”,最大限度地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在“淮南格物说”里,他说:“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既然身、天下、国、家同为“一物”,也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进而提出了“尊身立本”的思想。他以身为天下国家的“格式”,以身为本,以天下国家为末,家国天下跟着身走。他认为,个体是第一位的,没有个体,也就没有天下国家;个体之身不能修,天下国家也就不治,顺理成章地阐明了自己尊身立本的思想。王艮个人主义式的“尊身立本”思想的极致,是他提出了“明哲保身论”。据《王艮年谱注》载,他四十四岁时,“同志在宦途,或以谏死,或谪逐远方。先生以为,身且不保,何能为天地万物生?”这一以个人生命为第一位的观点似乎和儒家杀身成仁的社会责任感背道而驰,但决不能对此作简单化的理解。王艮重自身,不能与自私划等号,也并不意味着对社会责任的放弃,他是主张通过爱人、敬人、不恶人、不慢人的途径,保全自己,在此基础上去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丰富的内涵,值得我们去细细地品味和体会。 王艮的教育思想也很有特色。他有一句名言,叫做“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这里所说的“隐逸”,是指未曾做官的一般平民,“愚蒙”,是指知识贫乏的下层群众;而山林、市井是他们经常聚集的地方。他“入山林”、“过市井”进行启蒙教育,就是要把教学的基地从书院移入民间,使教育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中国的教育发展到宋明时代,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书院教学传统,比较著名的如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江西贵溪的象山书院、贵州修水的阳明书院等,宋明时期的思想家几乎没有不与书院发生关系的。书院教学内容上与下层群众相距甚远,感情上与普通百姓格格不入,实际上等于关闭了面向下层群众的大门。王艮与其他人的不同在于,他既继承了书院的教学形式,曾在复初书院、安定书院、南京的新泉书院、家乡的东淘精舍等处讲学,又不受书院传统的束缚,利用山林、市井、家舍等场所,积极开展书院外的教学活动,从而吸引了一批有志于学的劳动者。曾在王艮家中“请益月余”的李春芳叙述说:
见乡中人若农若贾,暮必群来论学,时闻逊坐者。先生曰:“坐,坐,勿过逊废时。”嗟呼,非实有诸己,乌能诲人如此吃紧耶!
由此可见,他始终与社会下层群众保持着密切关系。在他的学生中,虽有如徐樾这样的官僚士大夫,但更多的是布衣平民。如他最早的学生林春出身佣工,朱恕则是樵夫。在泰州后学中,还有陶匠、田夫、商人等等。由于王艮讲学传道的主要对象是处于社会下层缺乏文化知识的平民百姓,王艮就采用了简易快乐的教学方法,他要求学生象匠人斫木那样简练又自然地学习。他说:
天下之学,唯有圣人之学好学,不费些子气力,有无边快乐;若费些子气力,便不是圣人之学,便不乐。
由此,我们听到了他的《乐学歌》:
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呜呼!天下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
我们现在已经难以统计,那时侯究竟有多少下层社会的“愚夫俗子不识一字之人”跟随王艮求学,但从《乐学歌》轻松得意的语调里,应该可以感受到他不同寻常的感召力吧。 三、泰州风骨 有人说:“王艮从阳明先生哪儿借得了火,炼的是自己的金。”这话说得好。王艮的思想以阳明心学为源,却又不囿于此。理学家朱熹高傲地说,“理”为本。阳明不软不硬地说,“心即理”,这等于说,“心”是本。王艮听了老师的话,用“心”体悟了一会儿,来得更直接,他说,理不是本,心也不是本,人才是本。他在对儒学经典的“心斋”式解读中,实现了对传统儒家观念的颠覆。正是靠着这种敢于超越、不断创新的精神,靠着尊重人的天性和个人价值的理论品质,王艮让晚明社会卷起了一个泰州“旋风”,使十六世纪愚昧黑暗的中国出现一片思想生机。 这里,从泰州学派的角度,谈一点王艮思想的影响。 人们在谈到我国历史上魏晋时期的文学时,总喜欢用“魏晋风骨”来指称那个时代风清骨峻、正气凛然、悲凉慷慨的文学气象。文学是人学。这种气象何尝不是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特征?当我们慢慢靠近泰州学派这个思想群落,走进朱恕、韩贞、颜山农、何心隐、罗汝芳、李贽等人精神世界的深处,总感到有一种与魏晋名士相似的气韵在流动,在激荡。就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高扬自我、执著于道、慷慨赴死的崇高人格来说,他们是无愧于“风骨”这个名号的。 王艮那种抛家出游,数十年不安枕席,执著于道的使徒精神,在泰州后学那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让我们首先说一说泰州学派门下的两个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学人”——朱恕和韩贞。 樵夫出身的朱恕在一次听讲时,遇到了王艮的学生宗部,宗部怜其贫,赠他一笔钱,劝他另谋生计,以免砍柴之苦。但朱恕却不领情,他说,钱将激起我的营利之心,“子非爱我”,“子将此断送我一生”,遂将钱掷坏。以后,他又多次拒绝他人的馈赠。这种不求利禄,一心求学的精神,表现出对王艮思想的孜孜追求。从王艮处卒业后,他编写了好多通俗的诗歌,在下层群众中讲学。还收陶匠韩贞为学生,并引荐到王艮父子门下。 韩贞,号乐吾,兴化人,至今还悬挂在兴化四牌楼上的“东海贤人”那个匾额,说的就是他了。韩贞自幼家贫,以烧窑为生,仅有的三间茅草房,也因偿还债务变卖了,只好住在窑洞里,但他居不求安,淡泊名利,志向高远,深得王艮赞赏,说他“莽莽群中独耸肩,孤峰云外插青天。凤凰飞上梧桐树,音响遥传亿万年”,并以儒巾深衣相赠。韩贞学成归里后,着儒巾深衣,以“化俗为己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36岁时,名声大振,学子盈庭。他曾在别人的鼓动下参加科举,但看见考生们背着席、光着脚进入戒备森严的试院,他感慨地说:“大丈夫出则为帝王师,入则为百世师,……今治文如此求名,非炫求售,枉己而何?”于是,毅然归里,继续过他陶工加老师的生涯。
兴化韩贞墓 泰州学派执著传道的使命感越往后,越显得强烈和神圣。所谓“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即道出了颜山农等人的激进性质。 颜山农是王艮的再传弟子,王艮的“王学左派”(后人对泰州学派的称谓)进一步转向激进主义的“狂禅之学”,颜山农正是关键人物。 颜山农一生讲学、建会不辍,足迹遍及近江苏、浙江、山东、河北等地。他把一切道理与教条格式,都要打破,一切思想规范,都要推翻,将一切理学的道德说教和修养方法都看作妨碍“自然之道”实现的桎梏而应予废弃不用。这种否定一切的狂放姿态使他处于社会秩序之外,而被看作“铤而走险”的文化叛逆。颜山农出身民间,终身都是布衣,但他却时刻怀着“救人心病”、解救生活苦难的道德责任感,不管外在压力多么强大,他都无视无惧、放手直行,大胆地做他想做的事情。这位被黄宗羲称作“游侠”的江西汉子,最终被看作招摇惑众的妄人被捕入狱。在八十多岁的时候,又被流放边外,死于荒山野岭之间,但他那种任道直行的狂狭精神,却与青山同在。 就在颜山农在颠沛流离中去世后不久,他的得意弟子何心隐,在湖北孝感聚众讲学时被捕,并很快死在狱中。他与老师一样痴心于心斋之学,一生不辞辛苦地热心讲学,结局和他的老师一样地惨,骨头也与老师一样地硬。又是二十年过去了,泰州学派的又一传人李贽因有人告发他倡导邪说而被逮往京城。李贽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异端之尤”,他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叛逆性格和反抗精神,令当权者胆颤心惊。尽管他在狱中受尽折磨,但始终铁骨铮铮,宁折不弯。他没有像他的前辈那样,死在别人手中,而是趁着剃头师傅转身时,拿起那把剃刀,顺手从自己颈项间一抹而过,自颈殉道。他死得够壮烈!关于泰州学派,李贽在他的《焚书》中有一段话: 古人称学道全要英灵汉子。……当时阳明先生门徒遍天下,独有心斋为最英灵。心斋本一灶丁也,目不识一丁,闻人读书,便自悟性,……此其气骨为何如者。心斋之后为徐波石,为颜山农。山农以布衣讲学,雄视一世,而遭诬陷。波石以布政使,请兵督战,而死广南。云龙风虎,各以其类然哉!盖心斋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波石之后为赵大洲,大洲之后为邓豁渠。山农之后为罗近溪,为何心隐。……一代高过一代。 这话同样适用于他自己。而且,他,无疑是“一代高过一代”中最高的一代。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不重视个体的人的存在。儒家所讲的人主要不是指自我或个体,而是突出“众”、“群”、“民”,即人之群体或社会。泰州学派以对自然人性和个体价值的肯定维护了作为个体的“人”的尊严。 他们讲利、从欲、重情。如果说,王艮等人把以身为本定位在维护人的生命、尊严和理想上,那么,李贽更关心的是人的物质利益。李贽从自然人性论出发,宣称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所在,“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则知势利之心亦吾人禀赋之自然矣”。进而主张统治者应顺乎人的自然之性,满足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 在儒家那里,欲和理相对立。儒家较为重视人的精神生活,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忽略甚至反对人的物质欲求,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这种思想发展的极致。泰州后学认为,天理和人欲并不是截然二分的,天理就存在于自然而然的日常生活中。王襞指出:“鸟啼花落,山峙川流,饥餐渴饮,夏葛冬裘,至道无余蕴矣。”他们把人的生理欲望,看作道的呈现,宣称理即在自然人欲之中。重理轻情、以理统情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泰州学派的学子们主张在率性而动中释放人的情感,无论是罗汝芳的“赤子之心”,还是李贽的“童心”,都指的是自然活泼的至真至纯的性情。在李贽看来,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私奔,因情而动,是“善择佳偶”而非有违礼法。 在李贽这里,礼义已不再是理学家的道德规范,而是“发乎性情,止乎自然”的一种在解除了所有束缚情况下的人的情感的绝对自由的表现。在李贽等泰州后学的影响下,晚明文坛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情感主义思潮。于是,就有了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就有了《牡丹亭》中杜丽娘的为情而死,为情复活。在他笔下,情的力量是如此巨大。泰州后学不仅在理论上鼓吹性情,还在行动上表现出个体之间患难相依的深厚交情。颜山农好急人之难,赵大洲赴贬所,山农与之同行,徐樾战死沙场,山农寻其骸骨归葬;颜山农被捕下狱,罗汝芳狱中侍奉,六年不赴廷试。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真情,也许正是泰州学派的生命力、冲击力和凝聚力之所在吧。 泰州学派对人自然天性的维护蕴涵着对个人价值的肯定。更可贵的是,他们对个体价值的肯定不停留在口头上,更注重在对道的执著追求中去努力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在他们的执著追求下,“圣人”已不是难以达到的梦想,而成为人人可以拥有的头衔:罗汝芳称颜山农为圣人,杨复所称罗汝芳为圣人,李贽称赵大洲为圣人,李贽也被称为“可做圣人第二席”。“不说我该如何做圣人,却说圣人来做我。”从人人可做尧舜到尧舜即人人,体现了泰州后学的价值观念由群体本位向个体本位的转换。 由泰州学派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二者在对个人自由和价值的追求上存在某种相似性。“竹林七贤”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口号,超越纲常名教的束缚,提倡个性和精神自由,成为封建社会第一次自我意识的觉醒,但他们追求的似乎是一种离形去知、不为物役的绝对精神自由。比较起来,泰州学派的追求则要塌实得多,他们怀着人人可以成圣人的自信和自尊,挺直腰杆,积极投入到社会政治和世俗活动之中,在百姓日用之道中追寻真正的自由,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并以此去匡正世道人心。 由王艮开启的泰州学派,以其强烈的反叛精神和鲜明的创新品格,给十六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次大震动。尽管由于历史原因,它最终成为了昙花一现,但它表现出的对个体的人的尊重和鲜明的精神启蒙意义却化作一道美丽的彩虹,永远留在了历史的天空,并随着历史的进步而日益显示出价值来。 泰州,也因此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